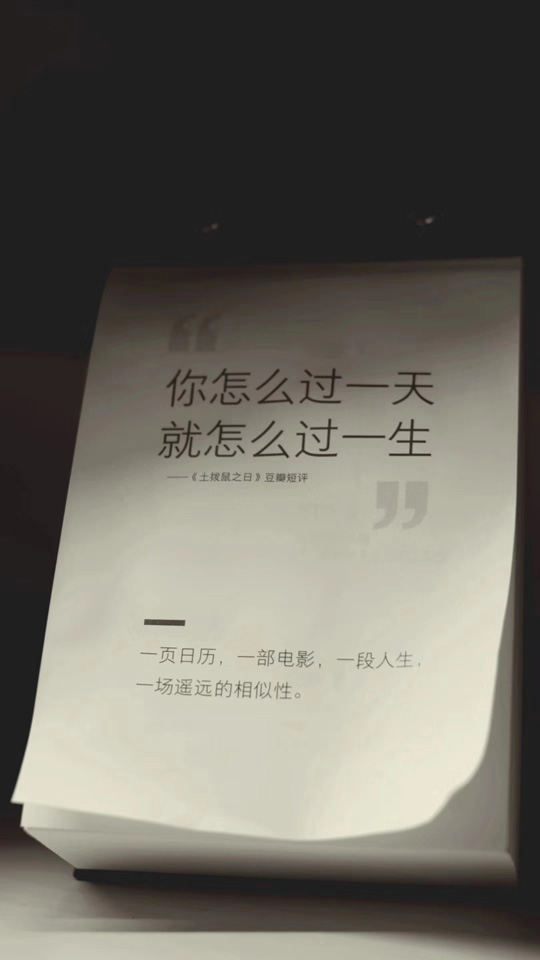一
我出生那天,他和父亲一同裹着家里唯一的那件棉大衣马不停蹄地给母亲送来了糖水鸡蛋。他刚进门,还顾不得拍落身上的雪花,便欣喜若狂地四处找寻,妈,小弟呢?小弟在哪儿?快让我抱抱。
这是母亲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最喜欢提及的一幕往事。那年,他6岁,我刚出生,尚未取名。后来,在一次通宵达旦的农活中,他消失了。母亲哭着我了整整一天,险些把茫茫田野翻遍,可还是找不到他的影子。
他真丢了。这一丢,就是整整19年。这19年里,母亲只要一回想起那个晚上,双眼里就注满了泪水。漫漫的19年尘世光阴,让母亲衰白了发鬓。但在她心中,从始至终都不曾衰老的,就是那一个我刚出生的风雪之夜。她无可奈何地将所有深沉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到我的身上。我的任性、顽劣、调皮,都被她面无怒色地一一隐忍下来了。
于是,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哥哥尚在的话,母亲绝不会这么毫无顾虑地纵容我。因此,我便有了这样狠心的念头,我希望,这个失散了十几年的哥哥,一生都不要再出现。
19岁的我要上大学了,临行的前夜,母亲忽然一面给我收拾行李,一面默默地流泪。她说,这家里最后的一个孩子都走了,以后我该怎么过?要是你哥在多好啊!如果他还活着,已经25岁了。
看着母亲悲凄的面容,我有些于心不忍。忽然开始想念这个仅有过一面之缘的哥哥。多年的田间生活,让母亲早早患上了严重的老寒腿,天气一旦阴沉,她就会痛得龇牙咧嘴,必须要有那么一个人,生着小火,不停地给她上药。我走了,家中只剩多病的父亲和孤单无助的母亲,谁来给她生火,谁来为她搓腿?
二
大学第一年,母亲打来电话说,前些年发出去的寻人启事有了消息。听人说,在两百多里之外的闭塞的山村里,有一个稍微比我年长的小伙子,和我长得很像。母亲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万一不是呢?
其实,此刻我的心里充斥着莫名的忐忑和挣扎。如果那小伙子不是,母亲定然要悲凄一段时日,她那身体,怎能经受得住几百里地的波折和内心无边的空洞?如果是,她的情感世界也必然要惊涛狂澜很长时间,那么多年的亏欠与内疚,定然会让她倾其所有,作为补偿。这样一来,我就会在一个原本温暖而又团圆的氛围里,遭到无形的冷落。
最后,挣扎了一夜,我还是让母亲去了。他们带上干粮和泉水,挨家挨户地找。后来,母亲在一个破旧的茅草房里看到了一个健硕的小伙,他虽然衣衫褴褛,但眉宇间却漾着一股凌人的英气。最要命的是,他的下颌上、竟有一颗豆大的黑痣!母亲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他的下颌处,也有一颗黑痣。
父亲也同时看到了那颗触目惊心的黑痣。母亲暗暗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问清楚,可热泪,还是滚滚如潮地洒了一地。
三
他的父母已经双亡。他似乎能够断定,自己就是母亲的孩子。他说,母亲让他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就为这一句话,母亲领着他,不顾寒腿的疼痛,硬是要把他带回家。
母亲为他纳鞋,为他做菜,给他取上从前的名字,面目自豪地带着他走街串巷,逢人便热情地介绍,那是他的大儿子。
年前归家,他与母亲一同站在出口等我。我提着行李箱从人群中拥挤出来,他愣愣地站在那儿,不曾认出我。后来,是母亲上来接过我手中的行李,他才慌慌张张要去帮母亲的忙。岂料,母亲竟说,不用了,这些年,你在外面吃过的苦已经够多了,家里怎么能让你再吃苦呢?
这一句平白的话,让我心生哀伤。他走了那么多年,回来后,得到的是母亲全部的爱。而我在家中为母亲分担了十几年的困苦和艰难,得到的,却是倏然的冷漠。
一路上,我很努力地要与这个肤色古铜、阔别了多年的哥哥亲热,却怎么也亲热不起来。
回程那天,他来送我,大雪如鹅毛一般洒满了他的头顶。我坐在暖气徐徐的车厢里,逼迫自己用一种冷漠的方式来与他告别。但我眼前总闪现母亲所说的那个场景,十几年前,他冒着寒风与大雪,为母亲送来糖水鸡蛋,只为抱抱刚出世的我。
他沿着铁路跑了很长时间。呼呼的白气从他的口里喷出来,像一串绵长的叹息。我坐在车厢里,看着他穿着草绿的翠大衣,在站台主摇晃着臃肿身子的狼狈模样,忽然泪落如雨。
再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我终于放下心中所有的顾忌,主动让母亲叫他来听电话。谁知,母亲说,儿啊,你大哥说我们也不容易,为了给你凑学费和生活费,他硬是不听劝,一个人到南方打工去了。
于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幅辛酸的画面:我的大哥,赤裸着胳膊,在灼灼烈日下为我的安定生活挥汗如雨。
四
毕业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南下看他。我原本以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应该是高楼大厦中的其中一闻,殊不知,竟是残砖破瓦搭起来的小工棚。我并没有畏缩心里的想法。我想替他做一个星期的活计,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切身感受一下,被兄弟疼爱的幸福。
我习惯叫他的名字,而他,也是怯生生地直呼我的小名。我说,休息下吧,让我替你一星期,这几年,你也累了。我这样一段极为平实的话,却让沉默寡言的他站在昏暗的工棚里,低声地啜泣起来。
工地的生活真苦。最可怕的是,四周根本没有任何安全的防护设备。当盖到第三楼的时候,因为要从木板上推一车砖而撑不住重心。我哗啦啦地从施工的木料上掉了下来。
迷糊中,看到是满脸惊恐的他,用工地的小铁车推着我,吭哧吭哧地在郊外的小路上飞跑。我在一片刺鼻的药水味中惊醒。鲜红的血,汩汩地输进我的体内。医生说,我失血过多,幸亏这个好心人把我救了回来。我咧开干瘪的嘴唇笑笑,指着床边的他说,医生,你错了,这可是我亲大哥呢。
亲什么大哥,血型都对不上,怎么亲?顿时,我天旋地转。而他则一语不发地站在那儿。
原来,他一开始便知道自己不是母亲的孩子,但作为一个孤儿,他被母亲这样的执著和大爱深深打动,他既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又想成全母亲的寻子之心,于是,撒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他将积蓄全拿出来,只为给我输血看病。我说,你真傻,半辈子的心血,就这么没了。你完全可以跑掉,没人会追究你,想想,那是我自己掉下去的啊。
他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哥不傻,哥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还是知道,兄弟是何意思。这兄与弟,本就是一个血脉相连的名字,既然你都说了我是你大哥,那兄怎么能撇下自己的弟?
哥啊……我抱着他粗糙的大手,忽然泣不成声。那因自私而抑郁了多年的愧疚、伤怀、思念,终于在伤痛中汇成一股呼啸的热流。
哥,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疼惜你。谁让我们的名字叫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