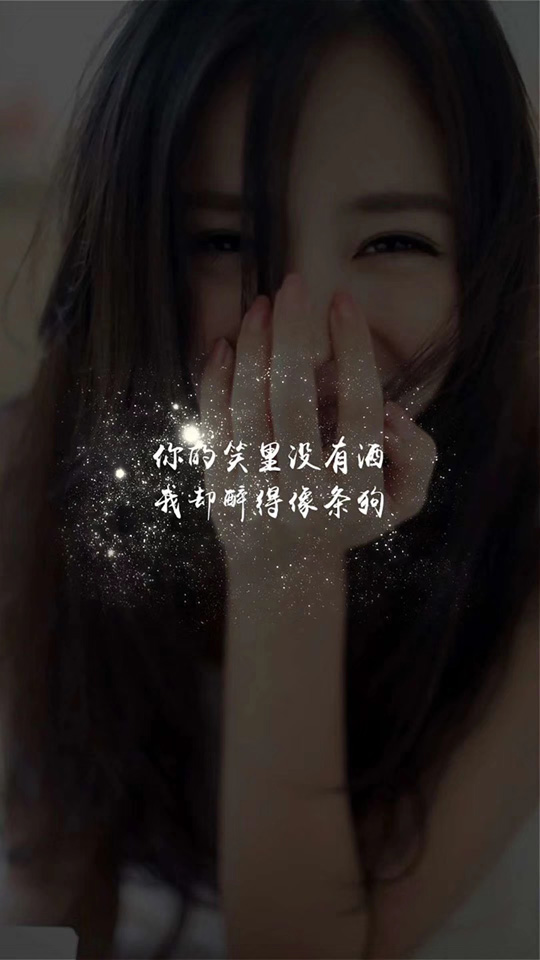雨丝斜斜掠过窗户,案前的诗书正停在“空山新雨后”。
指尖抚过泛黄的纸页,忽然觉出几分凉意。这初秋的雨,早在千百年前就被王维装进诗里,带着松间明月的清辉,在千年后依旧洇湿人心。
檐下的雨棚被雨滴打湿了声线,滴答声里掺着秋蝉的残响。
忽地想起柳永“寒蝉凄切”的词句,便多了几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缱绻心事。
秋色尚新,山色如故。
抬望眼,有水雾浸漫山野;低回首,有窗前花儿开欲然。
想起了邵雍的《初秋》:夏去暑犹在,雨余凉始来。我的初秋,也在一场立秋后的雨里展开。
有人说,初秋的韵味,向来是诗家词客所钟爱的。
这节气不甚冷,也不甚热,只是将夏的余威与秋的初凉,杂在一处,使人觉得既爽利又微醺,恰如饮了半盏清酒。
有人喜这初秋的天高云淡,蓝天如洗;有人爱这初秋的瓜果飘香,连风里都带着甜。
而我独爱,这初秋里的诗韵词工,在时光的素笺上,悄然洇开几行墨痕。
古人写秋,总带着三分清愁,七分况味。
杜工部写“露从今夜白”,白的不只是草尖清露,更是游子鬓边霜;李义山写“秋阴不散霜飞晚”,那朦胧的秋阴里,分明藏着欲说还休的心事。
而今我站在初秋的风里,看草木渐黄,听秋蝉声咽,恍惚间竟与千年前的诗人隔空对望。
不是我们都钟爱秋天,是这缱绻的秋意,从未改变。
孟浩然在《初秋》里说:不觉初秋夜渐凉,轻风习习重凄凉。
昨夜的一场雨,为暑气未收的重庆添了几分凉意。许久未曾开窗酣睡,却有路灯照窗台,恍若明月来相照。
许是这般,反倒久未成眠。
凉风习习,想那孟浩然写下诗句的心思,客居的诗人,总会因为一场雨,一阵风,一次天气变化,生出许多悲凉的情绪来。
而我在千百年后,在那些浅淡的字句里,一一捡拾他们的心事,就像拾起秋天的落叶。
有些落叶很美,有些落叶残败,有些落叶则带着欲说还休的故事。
一如那年,白乐天在曲江逢早秋,便有: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子。朱颜易销歇,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青芜与红蓼,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古代文人伤春悲秋是常事,而白乐天于早秋时节,再度重游曲江,青芜、红蓼如期绽放,只有自己这个看花人,游曲江的人,已不是去岁的模样。
时光流逝,容颜易老,倒让我想起那句“二十四桥仍在”,而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四时更迭,总有一些故事在时光里铺陈结局与新的开始,也总有一些人,在一片落叶的,一阵秋风里,一处旧景中,感怀往昔。
而秋,在千百年的诗山词韵里仍旧独树一帜,像一位执笔的丹青客,以霜为墨,以风作笔,在天地间挥洒出最动人的画卷。
而泛黄的书卷里,那些被秋雨洇湿的文字,正在书页间生长出新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