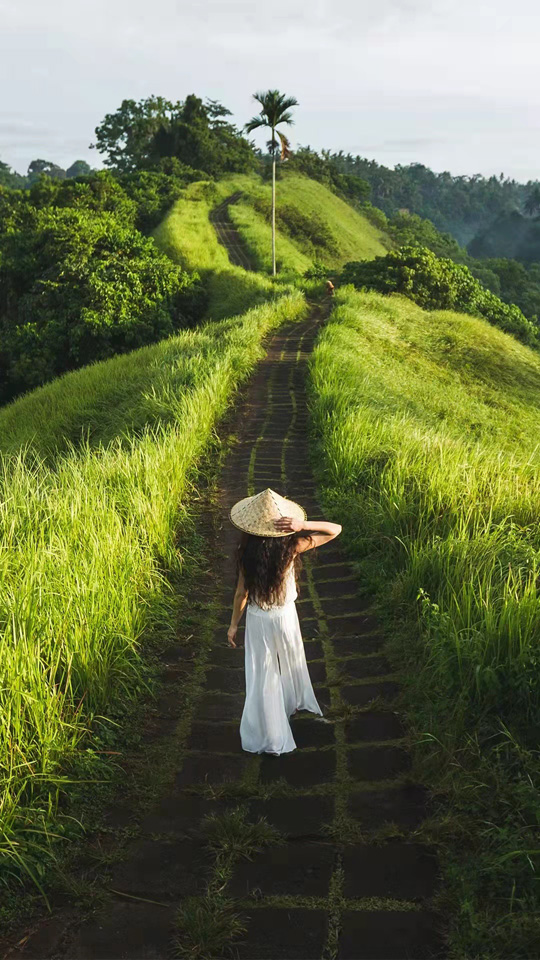1
在那张床上,我跟外祖母一起睡了六年多,从我一岁半至八岁,两千多个日子,我一直是跟外祖母睡的。那时,父母带着弟弟去远方养蜂,他们是赶花人,一年四季追赶着季节不断地迁徙,自然无法照顾两个孩子,只好把年长一岁的我留置在外婆家。于是,我整个童年都跟那个小山村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幢朴素的老屋和井栏边落满月光的庭院,那张雕花木床,截取了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某段生命时光。
那是一张普通的床,民国时代的婚床,木结构的框架,面板有三大块白骨镶嵌。中间一块是一出戏的场景,隐约记得有人牵着一匹马,路过一个凉亭,而两边则是花草。这些平常的东西固执地在我的生命中烙上剥离不去的胎记。
那时的冬天似乎每年都有雪,外祖母常常出去念经,中午赶回家给我做午饭。下午带我一起去,或者给我留下一个热热的火铳,顶住我别乱跑。有时我跟着边用朱砂点经卷,一边熟练地背着《心经》。无聊的时候,便在火熜里爆豆子。抓一把干豆子,埋在炭火堆里,盖上铜盖头,然后静静地等待。时间显得悠长,寂寞也长起来,大片大片的空暇任由我挥霍或者用来发呆。忽然,寂静里爆出“啪”的一声,豆子熟了。我并不急着打开盖子,就这样倾听者越来越密集的爆裂声。空气中逐渐弥漫出炭火和豆子的香味,使一种名叫孤独的东西越来越黏稠地在房中汇聚。
多年之后,当社会学家提出“留守儿童”这个名词,我忽然意识到我站在那么多留守儿童的前列。留守,还是幸福的,因为等候的人总是会回来的。
2
过年的时候,便不再寂寞。父母亲带着弟弟回家乡到外祖母家看我。弟弟和我玩得很高兴,说好晚上他也不回家。于是,外祖母早早地就把被窝焐热,给我们洗脸洗脚,让我们进被窝。我让着弟弟,让他跟外婆睡一头,而我睡在脚后头。我们两双小脚互相抵着,你伸我蜷的做游戏,或者在被窝里“钻地道”,把厚厚的棉被假想成某一处黑咕隆咚的山洞,而我们俨然是艺高胆大的英雄。等到玩得疲乏了,夜也静下来,窗外的一些声音显得悠远而渺茫。
夏夜歇息总是迟一点儿,外祖母习惯睡外边。她怕我翻身时把手脚挨着蚊帐,蚊子会从小孔里叮进来。临睡前照例要用煤油灯烫蚊子。记忆中的煤油灯有两种:一种是可以提的,铁皮制成的,里面放洋油,母亲又叫三楸灯;一种是放煤油的,罩一个玻璃罩子,上面不封口。外祖母用的是后一种。把文章敞开着,用蒲扇前前后后赶几个回合,外祖母迅速地把床的四角垂下粗麻的蚊帐,在床前重叠,然后塞进凉席下面。我偶尔会淘气地带几只萤火虫进去,让它们爬在床顶,模拟着属于我一个人的星空,如若有一个提着灯笼飞动了,那便是我欢喜的流星。
难挨的是没有电扇空调,那时的寻常人家,25瓦昏黄的光也很金贵,还常常停电。麻质的蚊帐又极厚,床上热得人睡不着。外祖母总是拿着一把棕树叶制成的蒲扇轻轻地给我扇风。一下,一下,很有节奏,我在一习又一习的凉风中睡去。节奏渐渐慢下来,她的鼾声隐隐响起。然而我是极怕热的人,有了凉风才好熟睡。外祖母的手一歇下,我又醒来,不安地在凉席上翻身,外祖母旋即又拿起扇子给我扇风。一个夏夜,外祖母不知要被我吵醒多少次。如今外祖母早已故去十多年,我回想起来,仍能想见她无数次在迷迷糊糊间拿起扇子为我扇风,又抵不住夜的沉寂与瞌睡的疲乏,摇扇的手愈来愈慢,愈来愈慢,终于缓缓地搁在了席上,那把蒲扇始终握在她的手中。这样的夏夜过了六年有余。父母和弟弟是流浪的风去往远方,而我成为植物在庭院中售后。分离的惊吓把断裂埋进我的生命,而外祖母一直在缝补。
第二天,当我醒来,外祖母早已起床,蒲扇就在我的枕头旁边,柄上似乎还有手心的汗渍。蝉兀自在窗外聒噪着。
3
我读师范二年级的秋天,外祖母病了。母亲起初没有告诉我得的什么病,好些事亲友们连外祖父都瞒着,我更是无从知晓了。后来,我知晓了也不惊奇。生病很正常,每个人都要生病的。单传的我没有去想一个老人病了意味着什么,及至我看到她,才惶恐起来。外祖母的皮肤都已经变黄了,说是因为胆管被阻塞,胆汁往外泛的缘故。
外祖母得的是胰头癌,已是晚期,一般皮肤泛黄后活不过三个月,最多不超过半年,外祖母当时已经七十八随了,这样的高龄不适合手术的。死亡,仿佛一下子临近了,令人束手无策。我不肯相信这个现实,因为外祖母出了皮肤之外,一切都没有变,她依然慈祥和气。而皮肤的颜色,看过几次之后,似乎也渐渐习惯了。我几乎幼稚得以为,医生误诊了,外祖母只是得了小毛病,她将这样一直活下去。
亲人们一直都瞒着她,外祖母许是隐隐觉出了什么。有一次她摸出挂在胸口的观音挂坠,说菩萨会保佑她。我一下子就鼻子酸了。她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而是寄寓信仰。更大的不幸是表姐的辞职。表姐原在广东医院工作,外婆吃的一种很昂贵的药都是她从广东邮寄过来的。但是当时因为体制和工资的种种问题,很有才干的表姐辞职下海做生意去了,外婆的药断了。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主张换一种便宜的口服液。天气热了,又没有冰箱,药开瓶之后,就用井桶吊在井里边。外祖母跟我说,上次服的药好,现在的药,没几天就有点酸味,怕是没什么治疗效果。我懂她的意思,可是,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父母常年举债,起初是养蜂亏本,而后是造房借钱,清贫的家境一直压迫着我们。
我最终所做的,就是偷偷地向一位已经工作的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瞒着所有的人跑到杭州去帮外婆买药,即使我的钱只够买一盒,我也要尽力让外祖母宽一宽心。18岁的我拿着杭州地图跑了好几家医院,都被告知没有。然后,我又跑到了宁波,一个个医院的药房都问下来,也没有……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自己已经长大,不仅仅是因为会有可以自己支配的钱,更重要的是我会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而不是被粗暴地斥责一声:小孩子少管闲事!那么,或许,我可以多做一些什么。我的外祖母,你为什么不能再多等几年?
因为终于没能买到药,心中觉得愧对外祖母,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不敢去看望她,我怕看到她日益消瘦的容颜和失望的目光。是的,我怕。至今,我也深深地愧疚着,这么多的外孙女中,我是她最疼爱的,她把我从一个嗷嗷待哺婴儿抚养成活蹦乱跳的小姑娘,给了我一个外祖母和一个母亲双倍的爱,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4
然而谁又能与死亡相抗衡?再见到外祖母,她已经躺在床上了,我很熟悉的床。曾经是外祖母和我的床,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花白而稀疏的头发披散着,没有人再为她夹一枝她喜欢的栀子花。生命力正无情地从她的身上流失,像一只沙漏不肯停歇地镂空外祖母的躯体。我捧不住那些流沙,它们从我的指缝间纷纷落下。
暑假的时候,我将去杭州进修美术。临行前去看望外祖母,她已经搬到大舅家里了。我在她的床前站了很久。她的手露在被子外边,瘦得知剩下皮包骨头,一些暗色的乌青触目惊心,是注射留下的淤血吧。外祖母总是这么忍耐,从未见过她骂人,甚至没有起过高声。即使到了病重时分,她也只是哼哼,不肯大声呻吟,也没有提过要求——包括治疗。当她疼痛难忍的时刻,家人请来郎中为她注射配来的杜冷丁,这种麻药可以减轻癌症的痛苦。
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一节一节地抚摸着。她的手指异常的僵硬,几乎无法伸直。我希望我掌心的温度能够温暖我的外祖母,让她在冗长而缥缈的睡梦中抓住一丝人间的气息。就是这双手,曾经多少次为我穿衣缝鞋,曾经多少次为我煮粥喂饭,曾经多少次为我扇风掖被,曾经它鲜活而生动,宽厚的手掌补全了我童年空缺的爱。而今日,它是这般了无生气地垂落着,仿佛一把欲断的枯柴。
外祖母一直都没有醒过来,我不知道她醒来是否还会认得出我,那几天,她的生命就靠流质食物维持着,牛奶或者麦片。时候不早了,外祖父催我动身。我依依不舍,这一区就是两个月,她还能等我回来吗?外祖父送我到门口,叹着气说:“唉,怕是真的不行了……她去年说想吃西瓜,总算今年夏天的西瓜吃到了,也该放心了……”望着他哀伤的眼睛和佝偻的身子,我感到深深的凉意。